
“他们”曾经就是我们:普里莫·莱维和铭记大屠杀
如果说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这三本书中藏有一整个宇宙,那么其中的冲突、人性理解的缺失和真实世界与可能性的深远就共同组成了其中的黑洞。《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在这三本书中,普里莫·莱维重建了那些无法重建的事实,讲述了那些无法言表的故事。他的笔下没有悲怅,没有情节主线,甚至没有主题。这位作家戳进了人类苦痛的最深处,在那里,目之所及只有一种叫作“罪恶”的东西。越过了这个边界,就是另一类虚无的他者——我们没法把他们看作人类、看作受害者、看作难兄难弟,甚至连冷漠麻木的靶子都不是——这道边界将有血有肉的个体和“人类机器”区别开来,和纳粹、恶魔的工具区别开来,和那些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手持毛瑟98K步枪的生物区分开来。
讽刺的是,莱维作品中的恐怖不仅仅是德国人暴行的后果,而首先是他们的构想。这些恐怖各不相同,对称映射、猝不及防,令人无法抽离,这些黑暗故事里既有宏大的计划,比如说希特勒的“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Reich)以及他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又低微琐碎到极致,正如莱维笔下集中营囚犯日常遭受的那些细碎、毫无意义的折磨,比如说早上起床解手时允许的时间太短、厕所太少。他们设计了一系列不足挂齿的折磨手段,比如说放射虫的惩罚,对莱维来说,这就是罪恶之花。凡此种种,让我们思考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呢?由此,所有的答案都回旋倒退,回响在仇恨的历史中。
真正奇怪也最可悲的,甚至有时候能提振人心的,是莱维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的那种多变性。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我们能获得最深切的感受:书中有四个滑稽可笑的人物,其中有三个人对集中营的生活作出的自然反应便是极端而剧烈的改变,而正因此,他们的故事组成了书中展示人性的余兴节目。他们的演出并没有登上什么盛大的舞台,也不会带来太多的启发性,就跟真正的穿插助兴表演一样,稍纵即逝。然而戏份越少,反倒越是衬出他们奇妙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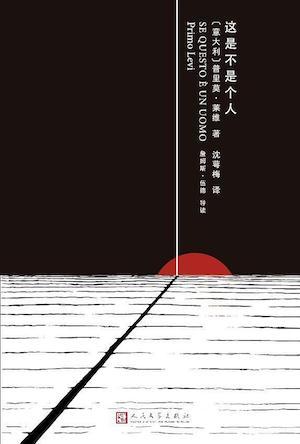
《这是不是个人》[意]普里莫·莱维 著 沈萼梅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3
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有一个名叫伊莱亚斯(Elias)的侏儒。他是一个疯子、一个傻瓜,在战前和战后,他“在外边”都是一个病人,然而在集中营的大熔炉里,他像是一个天生舒适自在的家伙,四处奔跑,干起活儿来力气能顶10个人。于是伊莱亚斯就好比一个攻城锤,猛地用脑袋撞上对手的上腹部——他的“敌人”全都是集中营的囚犯,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这个年轻人充分利用同情,作为一种生存的艺术,像变戏法一样将最基本的人类价值——比“价值”更深,应该说是人类价值的基底——转变成一把凿子,甚至是武器。
书中还有个铁皮人暴君哈伊姆·鲁姆考斯基(Chaim Rumkowski),这个犹太商人和纳粹勾结,将罗兹隔都(Łódź)置于股掌之下,号称是“犹太之王”。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鲁姆考斯基拥有决定犹太同胞囚犯生死的权力,还笃定自己就是他们的救世主,是一个“希律王第二”(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从属王,以铁腕和残酷著称)。然而故事末了,他自然也监督了自己的灭亡。
但这些鲜活的角色带来的所有快乐,也都消解在残忍的“解决方案”里,成为机械化种族灭绝的副产品。可是给我们讲故事的人——莱维却活下来了,这样一来,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不是都应该成为那个众矢之的?好像这就是他的目的,好像这就是他存活的理由。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道德上,还是逻辑上,他的幸存都让人难以接受。想想看,一个安然端坐写故事的男人和一个拼命保护自己饱受伤害、骚扰、折磨和饥饿的孩子们的母亲相比,哪个更有权活下去?亦或许他的幸存也无可指摘?我们也和莱维一样左右为难。这位作家已经永远被困在了这种难受的夹缝里,一方面活下来自己也没底,另一方面他也无法用生存无可避免来说服自己。
于是我们也摇摆不定。“我们读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本小说吗?因为它如此深刻,把我们拖进了一个宛若重铸的新世界,一个一草一木一粒灰尘都充满了邪恶和恐怖的世界。当然不是,书中记录的都是现实,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拍碎了我们塑造自我的所有的知识、感受和集体想象。这些现实撕裂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认知。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几乎都不愿拿起这本书。为了看完它,我们要借助各种滤镜——我们想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好让自己信服。其中有一些莱维也提到了,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不逃跑?”“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
还有一些人选择彻底绕开这些书,不过也许这并不明智。他们甚至会喋喋不休地提建议,说他们不想阅读关于大屠杀的文字,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当然,他们是对的。他们并不明白。但当我们拿起这些书的时候,其实是让自己卷入这种恐怖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黑暗和邪恶与莱维不同,而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我们要直面自己的怯懦和陷入困扰的可能性。从中我们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然而可悲的是,大屠杀的教训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或者说,我们并没有从中学到多少东西。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意]普里莫·莱维 著 杨晨光 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7-10
我们无休止地追求意义,渴望被那些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东西所吸引,被那些更宏大的、能够揭露现实的东西迷住——而这几本二百来页的书,无一不是揭露可怕而必须为人所知的事实。然而除了怀疑,我们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愤世嫉俗,对生活艰难这个现实再熟悉不过,因此也就不再需要这些苦痛来给我们更多人生指导了。
讽刺的是,我们并不那么天真无辜,也不像犹太人和其他受折磨的人一样容易触动,坚信不疑——这些人走向将他们运往集中营的牛车,被脱衣、被剥削,一层又一层、一丝又一丝,一句又一句话、一段又一段记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被降格成了牲畜都不如、低到地底下的生物。反观我们,面对着这段历史就显得天真无知多了,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是所谓“历史的受益人”,于是我们把脸扭过去,惘然不顾活生生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如今只能在诸如莱维的作品这样的书本中找到了。于是,我们的弱点被放大了。我们明白这些事曾经发生过,并且坚定地希望历史不要再度重演。我们的警示口号,“不再重演”就是我们盲目依靠的马其顿防线,没有呼吁行动,而只是宣示信念。
起码那些拥有“特权”(用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话来说)沦为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根本没法预见这种事发生的一丝可能性。他们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处境,即便大多数情况下毫无意义。我们并不想了解事实,但同时也在继续消费着那些保证畅销的关于大屠杀的书,阅读着里面清晰分明的事实。我们在纪念碑、纪念馆面前自拍。我们嘴很甜,发出声明,但随后是无尽的沉默。我们躲在这么一个观念背后——不管历史是不是如此,起码我们的人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线性的,而且永远在上升。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异常值,比如说疾病或者意外打断了这条线,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只要置之不理就行了。
有一点是人们绝对不会接受的——我们也可能成为“他们”,成为那些拥有“特权”,不仅沦为那些疯狂人类机器和他们98K步枪的囚徒,更要忍受困在集中营里的滑稽怪胎。“他们”曾经就是我们,这种想法我们并不接受,以后也不会改变。当我们笃信不疑,明白自己不可能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甚至是幸存下来的人)擦出任何认同的火化,我们就已经把这段历史忘记了。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