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重量:脂肪的文化史
“肥胖”这个词带有社会、文化和视觉期待方面的贬义,但它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词。尺寸通常被认为是越大越好:不论是在美洲——“伟大的国家”暗示着巨大且无可匹敌——还是在印度次大陆,“大人物”和“小人物”不但用于描绘身体特征,也体现着人物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正如克里斯托弗·E·福斯在他的新书《脂肪:生命物质的文化史》(Fa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tuff of Life)中告诉我们的那样,脂肪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构成了人类饮食的三大基本元素,脂肪这种营养物质的文化含义随着农业、宗教、文化、医疗以及现今媒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福斯研究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约三万年前的维伦多尔夫维纳斯雕像,一直到二十世纪,人们对肥胖身体的描述,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社会对肥胖身体的态度变化。对远古先民来说,使用动物的每一个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分解尸体来提取脂肪和营养丰富的骨髓,并尽可能多地从屠杀中获得脂肪。动物脂肪提供了家用灯火,还能应用于从制衣到医疗的所有领域。在幸存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原住民那里,他们的传统赋予内脏周围、特别是肾脏周围的脂肪以神秘的属性。对于生活在严酷的冰河时期的社会来说,肥胖不一定与生育有关,而是与成功生存有关,因此受到尊敬甚至崇拜。
随着冰川消退和农业社会的出现,脂肪和生存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变化。饲养牲畜标志着我们看待变胖这一现象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这是富足的象征,但也是即将到来的厄运:“吃太胖就会被杀掉。”到苏格拉底的时代,脂肪已经深深地与营养、成熟、腐坏的有机循环联系在一起,肥胖以前受到尊重,但是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肥胖开始代表一种没有柏拉图所说的“更崇高的愿景”的基本生活。福斯推测,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肥胖的身体表明了身体主人的“道德松懈”,这可以从饱餐、无能、腐败的罗马政治家和斯巴达战士之间的对比中看出,斯巴达战士因其严格的禁欲生活方式、男子气概和军事实力而受到崇拜。
随着罗马帝国衰落,基督教在西方出现,人们对肥胖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灵魂和来世,而肥胖则代表着一种尘世的、沉重的、肮脏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不可取,还带有着动物性。十字军东征开始后,对于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来说,对身强体健的战士的迫切需求以及来世的荣耀都得到了保证。对于一个在中世纪周期性饥荒阴影下辛苦劳作的人来说,这种物质和精神的流转是一种诱人的想法。新教改革进一步鼓励他们将基本的物质存在与更大的人类形式的观念区分开来,物质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尘世和污秽相关联,与来世等候着的完美生活截然分开。1602年,多米尼加牧师托马索·坎培拉建议城市关闭大门,禁止肥胖人群进入,身材走样的14岁儿童应该被流放。同一时期的其他神职人员甚至认为,选择性繁殖可以消除社会中的肥胖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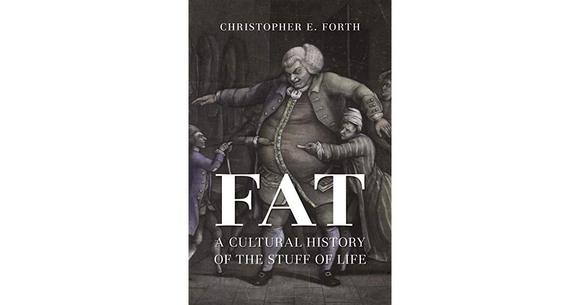
《脂肪:生命物质的文化史》
启蒙运动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脂肪和肥胖的方式。中产阶级出现了,他们对自我控制和自我提升的强调,不仅使他们进一步远离底层穷人,而且将他们封闭在家庭、庄园甚至衣服里,这有助于使他们提升至更高的社会地位。体重和测量变得标准化,允许人们用以前不可能的方式量化他们的身体。由于城镇生活让他们远离了大城市的饮食和卫生现实状况,人们开始提倡吃“洁净”的食物。
针对19世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身体观念的演变,福斯的分析尤为出色。日益显著的是,在其他大陆看到的体型——尤其是非洲和印度——被贴上了道德低劣和粗糙的标签,即使是不那么让人反感的对象,比如1877年亚历山大·阿勒代斯小说《太阳城》中的“印度佬”,“他那肥胖而油腻的身材,是其膨胀而狡猾的道德天性的绝佳外壳。”这不仅表现了西欧人对他人的看法,也表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女性被要求保持整洁、苗条、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要惹人注目。这种重压日益增加,就像女性在拼命努力让社会更加关注自己一样。被监禁的女权主义者的绝食抗议和被强迫喂食的遭遇,与遥远的伊斯兰教女眷居室里蜗居的肥胖女性形成鲜明对照,她们每天的目标就是消化尽可能多的食物,通过获得“理想的”体重,变得丰满而撩人。
20世纪日新月异的变化,为这本信息丰富的新书提供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结尾。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和美国精神的灾难性影响,我们与迅速演变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医学和现代生活的需求,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促使着西方无止境地追求柏拉图最先提出的那种轻盈感。变瘦就是超越了身体的需求,也就掌握了身体对满足和快乐的需求。《脂肪》是一本研究深入而有力的书,它学术性强,语调严谨。但偶尔会失掉更大的格局,读来不难感觉到,在某些地方,比如关于20世纪理想身形的部分,这本书不免有堆砌材料之嫌。但它仍然及时提醒着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作为有机体的周期循环。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