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作家大卫·华莱士-威尔斯:21世纪的元叙事是气候变迁
时值2100年。美国已经被气候变迁摧毁。超强的飓风不时席卷海岸边的城市,山火已经把洛杉矶翻来覆去地烧了好几遍。在夏天的某些日子,出门是异常危险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有被活活烤熟的风险。
在如此这般的一个世界里,我们是否会放弃历史进步的理念?我们现在还能对它深信不疑吗?美国作家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在其新书《没法住人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中,探讨了何以全球变暖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体验,更会左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理念和哲学。他最近表示,气候变迁今后可能会令我们相信,历史是“某种促使我们倒退而非进步的东西”。
“主导21世纪的将是气候变迁……正如现代性或工业主导了19世纪的西方,”他说,“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领域能免受它的波及。”
我(指本文作者、《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Robinson Meyer,主要关注气候变迁和科技等领域)近来与华莱士-威尔斯有一次对谈,内容关涉到他的新书、围绕气候变迁展开故事写作的困难性,以及他深信不疑的科幻小说预言之最终应验。谈话记录经过编辑,以求清晰和简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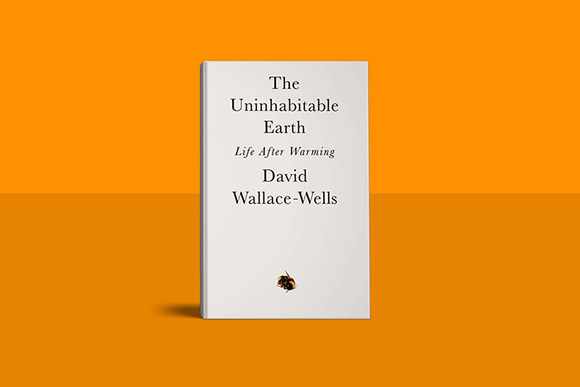
《没法住人的地球》
罗宾逊·梅耶:你在纽约创作了宏大的封面故事,接着又写出了一本书。写一本书也许没有写第一个故事那么容易保持简洁,对此你有何心得?
大卫·华莱士-威尔斯:之前我写了一个关于蜜蜂之死的封面故事,但还没有大量地、直接地牵涉到气候方面的写作。我的想法有点剑走偏锋,这说明我的背景正好适于写这种故事以及这本书。这方面我完全是个新手。我跟那些在这方面投入了毕生精力的人有不同的眼光——比如,我不会直觉性地把跟自然本身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关注范围,因而我在故事里也没有写到诸如动物的绝境或雨林的悲剧这类东西。我聚焦于人。
在第一篇里,我关注的是最坏的情况。我考察了全球气温上升4度、5度、6度乃至于8度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加紧向广大公众介绍这些情况,因为他们之于气候变迁,甚至于连广义的、主流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都还根本没有达到。
这让我想到,甚至于学界目前都还没有开始认真思考气候变迁的全部下游效应。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认肯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也许是不稳定的,它可能会在此处或彼处惩罚人们,但从全时段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能见证进步,见证更加繁荣、安全和健康的生活。
不过,我也不认为气候变迁会让我们前功尽弃,我只是觉得它很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尤其处于可设想性范围内的是,损害将累积到相当可观的地步,进而令我们彻底放弃历史永远指向进步这一观念,并开始视其为某种相对不那么可靠的东西,乃至于某种促使我们退步而非进步的东西。
梅耶:我想在这方面再延伸一下,但我首先还是比较同意对气候变迁的“广义的、主流的理解”,对此我也有不少思考。在你看来,所谓的广义理解究竟指什么?
华莱士-威尔斯:它变化的速度很快。我觉得我的文章在其中只有很小的影响,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则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它看起来确实引发了相当程度的警觉和焦虑,而且邀请到了一些科学家来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不过,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最触动我的是学术研究成果和大部分主流出版物所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巨大差异。差异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关乎变迁的速度。人们一般喜欢强调变迁速度的缓慢以及因其不具紧迫性而产生的对治之困难性。但我注意到一个鲜活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产生的所有碳排放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过去三十年来燃烧的化石燃料。我因而改变了自己的眼光——我意识到,这种状况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的。
第二点是,我们对它的范围有某种误解。大部分叙事都聚焦于海平面上升和南北两极的冰川融化。这显然是气候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样也带来一种错觉,那就是问题的影响只是地方性的——是不是只要离海岸线远一点就安然无恙了。
第三个问题是严重性。科学家经常把全球气温上升2度这一阈值视作气候灾祸的某种有意义的标志,我想,大部分读者也都会觉得,情况无非就是坏到这样的程度了。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度的上升幅度只是我们可能达到的梯级之一而已,根本不是天花板。
梅耶:你在书里也有跟许多以气候变迁为主题的学术类或者人文类写作打交道。谁的作品最吸引你?
华莱士-威尔斯:那些以气候政治(politics of climate)为写作主题的人——尤其是气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就好比是我的北极星。杰德·珀迪(Jed Purdy)的著作——他的学究气要强不少,但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将气候的挑战置于政治哲学的漫长传统当中来加以考察。
坦白说,这些作者及其著述中最让我有灵光一闪的感觉的,是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及其《大乱局》(The Great Derangement),它与叙事有关。我不同意他的多处解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有文学的背景。以前我在《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工作过一阵,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能有些不一样的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为何没有关于气候变迁的长篇小说佳作这个问题,我有一套不同的解释。
梅耶:他认为气候变迁的故事是特别难写的,对吗?你具体在哪个地方不同意他?
华莱士-威尔斯:高希的基本论点是,长篇小说这种体裁主要关乎个人的内心生活。气候变迁的问题对他来说完全属于另一个范畴。你可以把一系列个人的故事放到这个背景里,最后出来的结果类似于《后天》,其基调侧重于描绘某个面对艰难挣扎的人,但故事本身又跟气候变迁有关。这种不连续性给人一种陈词滥调、重复啰嗦的感觉。

《后天》剧照 图片来源:Twentieth Century Fox
我更倾向于从责任与恶行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巨大难题,那就是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共谋者身份(complicity),即作为此类长篇小说之读者以及对气候变迁感到好奇的西方人。我们巴不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进而希望我们在讲述气候故事时不要太夸大过失一面,并告诉我们那不过是我们文化中的其他某些人的问题,处于叙事之外。
在我看来,这种心态经常表现为妖魔化石油公司。我并不认为石油公司就是什么一心向善的力量,但我也认识到,在我买机票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并没有沦为石油公司的傀儡;在我吃一个汉堡包的时候,我同样不是这种傀儡。一切人在现代世界中的一切生活方式几乎都会留下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消费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译注),而我们也因为这一损害而共享着某种责任。
我希望诸如此类的启示将能激发人们去组织某些集体行动。较之于政治行动和组织化,生活方式选择这种东西说到底很渺小,在我看来它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消遣。但我也没有真的以一名倡导者(advocate)的身份来处理相关的主题,我的身份是真相讲述者和故事讲述者。
梅耶:依你看,是否有一种可以将那种叙事写下来的办法,但同时又不至于产生类似于《丛林》(The Jungle)的感觉?这本书以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者集会结束,叙事本身被吸收到群众的热情里面去了。另外,我觉得《抱歉打扰》(2018年的电影)也很不错,但它的情节跟《丛林》差不多,最终救了主角的都是政治。
华莱士-威尔斯: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想要在叙事里看到争吵还是人性。我真心认为,我围绕这个主题的写作有一个关键特点——但愿这不会给人大言不惭的感觉——它表明,如果你处理得当,光是简单堆砌事实就能产生巨大的叙事力量。许多以气候为主题的作家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去谋篇布局。
对于如何就这一问题讲好故事,我们的探索仍然处在相当初步的阶段。我想,往前看的话,更有趣的叙事形式很可能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并且用类似于剧场里演戏的方式来加以呈现。举个例子,不妨设想一座气候难民营,故事围绕营里的两个看起来跟罪犯无异的(quasi-criminal-like)人之间的争斗而展开,或者讲一讲度蜜月的人们如何在被淹没了的迈阿密海滩潜水。
有很多富有想象力的剧场可以用来演绎气候变迁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开始探索它们。然而,如果只有乐观的、充满希望且侧重于强调我们如何能解决问题的故事讲述才算是“负责的”,那就不过是——从叙事的角度看——另一种陈词滥调。最优秀的气候故事讲述者,是诸如巴拉德(J. G. Ballard)、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或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这类作家,他们明白这些力量将会以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奇特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
梅耶:吉布森最近出版了《边缘地带》(The Peripheral),它相当漂亮地告诉我们如今应当怎样去谈论历史——这涉及到在进步出现失误之后,日常的生活状况将是何等样貌,彼时人们尚未从之前的大灾难当中恢复过来。
华莱士-威尔斯:我在《巴黎评论》的时候曾经访谈过吉布森,故而对他还算略知一二。几个星期前我俩还互通了电邮,我有种在最后时刻加紧续写一本书的感觉,我们讨论了科幻作家如今愈发被视为气候变迁的先知这样的问题,他的回复就类似于——你懂的,每当人们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从来没有成功预测过任何东西!我们所有的预测全是错的。我们惟一做对的地方是描绘那种氛围(mood)。”我的回复则类似于说,不对,氛围本身就是一种预测。它是一种异常重要的预测,而你们的应对也极其正确。
梅耶:气候变迁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它是否还牵涉到别的一些方面?譬如说历史或其它一些东西?
华莱士-威尔斯:一个简短的回答是,我认为21世纪将是气候变迁的天下,正如20世纪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天下,而19世纪之于西方人而言则是现代性或工业的天下——这将是未来数十年里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生活的领域可以免受它的波及。人们经常把气候变迁说成是全球性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开始具体到个人生活的层面来探讨它的诸多意义。
我的基本看法是,这颗星球上一切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东西,都将会被这一力量改变。就算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喜人的,我也仍然认为,我们难以想象未来几十年里这些力量主导世界的具体方式,我们根本还没有下功夫来思考这些东西。
我算是个在纽约长大的美国90后。就此而言,我也是历史终结的产物。我能感受到世界上的各种力量在我的身边交错流动——尽管我对它们持怀疑论态度,尽管我对它们多有批判,但我还是相信它们将带领我们前进到一个更美好、更加繁荣且更加正义的世界。我知道路途艰险,但也知道我们必须尽力奋斗,以确保诸如市场力量和全球化这样的东西能够有利于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我明白过程当中少不了各种政治斗争。但总体上讲,我有一个相当情绪化的、高度直觉性的想法——也许我连公开承认它的意愿都没有,因为我会觉得那很尴尬——即历史确实是向前的,而我的生活也将是见证进步的一生。我有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今后不会再这么看问题了。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