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相贩子》:现代新闻的危机与转机
对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而言,有两样东西应归功于大卫·哈泼斯坦(David Halberstam)及其著作《媒介与权势》(这部出版于1979年的巨著检视了四家影响力巨大的新闻机构):第一是她的职业生涯。哈泼斯坦的书促使她立志要当一名记者,这条道路通往《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工作。在那个岗位上呆了三年后,艾布拉姆森被辞退。此时这本书又令她得以重整旗鼓。审视一番她曾负伤的战场后,她发现高品质新闻的未来错综复杂。艾布拉姆森想要效法哈泼斯坦此前在媒体界黄金时代的创举,为焦虑时代的新闻把脉问诊。
以类似于哈泼斯坦的思路,艾布拉姆森考察了当前陷入困境的四家公司的命运,如其所言,“为了让诚实的新闻存续下去。”她的新书《真相贩子》(Merchants of Truth)结合自己与BuzzFeed、Vice、《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打交道的相关经历,述说了自己近十年来在新闻界的见闻与思考。与哈泼斯坦选择的四家机构(纽时、华邮、CBS和《洛杉矶时报》)相对应,艾布拉姆森也认为她所考察的四家新闻机构都是优秀且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并且,“这四家公司目前正处于危机中。”
尽管就新闻谈新闻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艾布拉姆森的书仍代表着一种独特且富有雄心的尝试,她想要实现一种综合:一面总结这一时期里翻天覆地的变迁,一面协助我们理解产业巨头们——配角还包括特朗普总统、为谷歌新闻编写代码的程序员——究竟是如何为我们炮制信息大餐的。不妨设想一个场景,格雷汉姆家族、索尔兹伯格家族(二者分别为华邮和纽时的大东家——译注)与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且“不修边幅”的某男性杂志——即Vice的前身——创始人齐聚一堂、共商大事,各方都就新闻界的未来提出自己的主张。艾布拉姆森为其新书谋篇布局的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建制派与叛逆派媒体分别占据同一条跑道的两端,各自在抵达对手高度的同时也面临根基不稳之虞。传统的新闻编辑室在理解互联网及其带来的冲击时可悲地慢了不止半拍,在汲取创新点子来回击其年轻的竞争对手的同时,却依旧免不了迟钝和傲慢。新媒体机构通常以富有创意但也不无机会主义色彩的面目示人,它们的新闻编辑室一度名声鹊起,或以全新的广告策略先声夺人,但接着就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栽了跟头,其中某些问题是伦理上的。
从某个层面看,艾布拉姆森的书是写给新闻界的情书。书中最受敬爱的角色是记者,他们的言行事迹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彰显,另有一些与四家公司相关的、不无街谈巷议色彩的刻画。简单介绍一下记者们:艾乐·里夫(Elle Reeve)曾经在电脑工厂打工,关于夏洛茨维尔抗议活动的视频报道流传甚广,称得上是“有道德清晰性”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霍尔德(David Fahrenthold)是一名调查记者,他无情地揭穿了(“像一条寻血猎犬一样”)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的慈善谎言,并因此而获得了普利策全国性事务杰出报道奖。迈克尔·巴巴罗(Michael Barbaro)是“纽时新锐中的柏拉图式典范”——他身兼政治记者、播客主持人与作家三职,文笔优美,在特朗普胜选致使“总统女士”(Madam President)头条遭受当头一棒之际(这里当指《新闻周刊》在大选临近结束时曾准备过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人的胜选特刊一事,希拉里版的标题为“总统女士”,特朗普版为“总统特朗普”——译注),改写出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之夜报道。克雷格·西弗曼(Craig Silverman)持续不断地对BuzzFeed进行追踪报道,认其为“媒体界里在假新闻问题上的第一专家,时常走在其它媒体的前面。”
在频频送上情人礼物的同时,艾布拉姆森也对某些管理人员的失策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评。依照她的描述,转售予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之前的《华盛顿邮报》曾有过一段黯淡的光景,管理团队为适应全新的新闻经济而艰难挣扎。《前路漫漫》(The Road Forward)这份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备忘录在某场内部会议后流出,引发了轰动。“备忘录的标题固然表达出理想愿景和东山再起的期许,但实质性的路线图却完全缺位。”艾布拉姆森写道。
艾布拉姆森注意到,数位领域的创业新秀在优化其报道能力并以远超其传统竞争对手的速度发展其受众群体的同时,于确立新闻规范这一方面却显得步履维艰。在BuzzFeed这台高效的病毒式传播机器首次加入新闻栏目时,曾有评论称此举为“一场可行性实验,看能否在不考虑新闻伦理(诸如归因、可问责性等)的情况下将新闻部门嫁接到自身的运作中”。艾布拉姆森指出,BuzzFeed曾私下删除过逾4000条推文,且面临抄袭指控,堪称“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篡改活动(redaction)”。在通过禁止相关行为的伦理规范前的第四个月,年轻的BuzzFeed天才编辑本·史密斯(Ben Smith)删掉了该网站上三条批评这家企业的推文。“问题不在于推文是否真实可信,而在于它们对广告商不利,”她写道,“在意识到事情败露后,史密斯恢复了被删的推文并以邮件形式低调致歉。‘我当时的反应过于冲动了,’他承认说,‘我这样做是错误的。’”
在艾布拉姆森写书的那段日子里,《每日野兽报》(The Daily Beast)和《纽约时报》接连报道了Vice内部蔓延无度的性侵行为,但她对此的解释从许多方面看都是最丰富、最立体的。她撰写和编辑长篇调查报道的多年经验,在刻画上述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Vice首席执行官沙恩·史密斯(Shane Smith)和他的一帮“哥们儿”尽管创立了估值达60亿美元的公司,实现了常人望尘莫及的理想——透过向年轻人提供流媒体视频来盈利——但同时却鲁莽而冒失地颠覆了工作场所的诸多规范,包括禁止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员同床共枕的规定。其中一个令人心碎的桥段是,一名年轻的制作人在试图参与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某场颁奖礼时遭到了阻挠,而她的某篇报道就在获奖行列之中,她曾经与之发生过关系的上司则将娶她为妻。
尽管艾布拉姆森承认地方新闻已经无异于扶不起的阿斗,但这无非是一种马后炮。该书沿着阿西乐走廊(Acela corridor,沿着美国东北走廊延伸的一条高铁——译注)一路旅行,偶尔会到访西海岸,但没有考察冲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那股力量对地方新闻产业有何影响。在书的终章,她引用了一名明尼苏达州记者的话,此人“为地方新闻的惨状未能引起更大关注而感到愤怒”,鉴于该书同样不曾关注此事,这处注脚显得不无讽刺意味。平心而论,艾布拉姆森一开始肯定不想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但这确实体现出她在模仿哈泼斯坦时的一大局限性,后者的书诞生在一个较少碎片化、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美国地方新闻的衰落乃是整个业界的危机,我想,艾布拉姆森的书正好也印证了这一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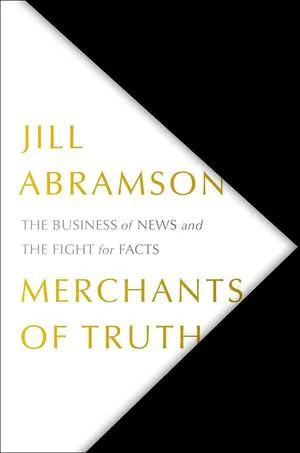
《真相贩子》
《真相贩子》的校样本被指在若干主题上有不准确之处,其中一部分已在最终版里得到修正。《纽约客》在访谈中曾就相关事宜向艾布拉姆森发问,答复是该书经过了事实查验,但“没有时间”来收集每一个受访者的反馈。
部分针对此书的早期评论尤其聚焦于艾布拉姆森在其母校讲演期间对政治新闻所提出的一系列批评,此类评论为数不少。她称2016年大选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毫无疑问是反特朗普的”,并主张迎合自由派听众能为其带来一笔“潜在的财富回报”,此说与她批评该报对希拉里“邮件门”的报道有过强的敌意有不一致之处。此外,她也为新闻编辑室里逐渐萌发的代际分裂感到不安,生怕腐蚀了报纸追求公平的信条。“一些更‘清醒’(woke)的人认为,紧急时刻要求运用紧急手段;面对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危险性,不用死守旧的标准。”她写道。不过,虽然她提出了上述一系列警告,但同时也承认纽时和华邮之间的新型竞争令两家报纸都取得了进步。
“《华盛顿邮报》强势回归。”她盛赞新东家贝佐斯及其新任主编马丁·贝伦(Martin Baron)。至于继任者迪恩·巴奎特治下的《纽约时报》,她总结称,“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闻报道从未如此壮大过。”
艾布拉姆森深为担忧的一点是,新闻人和商人合流的现象日益突出,靠着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线大肆敛财(这种担忧直接表达在书的标题里,即“真相”和“贩子”出双入对)。她将“原生广告”(native ads,也称“植入性行销”,其典型便是所谓的软文,或某些外观与一般信息几乎无异的“受赞助条目”——译注)斥为业界里的“新型数位科学怪人”——企业营销和新闻报道的高度相似性令读者易于上当受骗。BuzzFeed和Vice这类商人开了不少创收项目的先河,传统出版业也随之跟进,在自家广告的栏目里搞起了这类东西,艾布拉姆森称此举令以往区隔新闻与商业的那道高墙“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对此不无哀叹。
这些观点毫无掩饰地表现出了艾布拉姆森的自我形象:一个竭力想要将两个时代缝合起来的编辑,乐于接纳数位时代的诸多发明创造带来的利好,但对一切有侵蚀传统新闻价值的事物抱有高度的怀疑。对于不愿见到自家新闻编辑室搁浅的编辑们来说,目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时刻。要想存亡续绝,发掘自己在原先职业生涯中未曾接触过的新型合作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艾布拉姆森一度也为此绞尽脑汁。内部资料《纽时创新报告》(Times Innovation Report)被泄露给Buzzfeed一事——一场新媒体大败传统媒体的年度大戏——表现出这间新闻编辑室资质优秀但却高度僵化的一面:它经常将数位创新斥为“不符合纽时精神的”。
艾布拉姆森带着沉痛的心情反思了这段动荡时期。“我不觉得技术变迁应该引来道德变迁。我要反击回去。可能我的原则太僵化了;也可能为了拯救《纽约时报》就必须软化一些传统的教条。”
从全书来看,她对自己失去工作的解释算是一种微型的个人回忆录、一种对往事的忧郁回忆,2014年时艾布拉姆森被炒一案一度令舆论哗然。当时曾撰文报道此事的记者阿曼达·邦妮(Amanda Bennett)注意到,对女性而言,艾布拉姆森被炒“无异于一道闪电打在导火索上”。我想,这本凝结了艾布拉姆森对该时代首次全方位刻画的书,应当能重启一场对话。她坦然描述了工作中的孤独感和压抑,以及来自高管的异化感。尽管对自己的薪酬低于男性前任一事表示愤怒,但她仍对自己的失策持批判态度,不同酬一说后来在《纽约时报》引发了争论。
一个令人相当苦恼的桥段是,曾经将她提拔到原先工作岗位上的出版商小亚瑟·索尔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向她的上司提交了一份书面评价,此评价后来辗转流到了艾布拉姆森手里。“这封信的辞藻极度个人化,把我说成是喜怒无常的,还援引了我最亲密的同事的意见,说我是个很难打交道的管理者,”艾布拉姆森回忆道,“它根本没有谈到我工作的实质或者质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封信的主旨,那就是‘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坏女人。’”
四个月之后,她正式离职了。“我连个房屋经纪(stellar manager,这里的Stellar当指纽约著名的房地产巨头——译注)都不如,”她四年后承认说,“但我也是双重标准的受害者,与许多女性领导人无异。”
她补上了一句,“到最后,跟我同时代的所有记者都会沦为玩蒙眼躲猫猫游戏(blind man’s bluff)的过渡性角色。”媒介的权势届时将只是过去时。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