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词从何时变成了文学?
当歌词变成文学时会发生什么?它失去了音乐的陪衬,却也能焕发出另一番光芒。它那迷人的旋律仍然留存于字里行间,然而纸张周围的留白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就像白噪音一样。
当然,这个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歌词毕竟是歌词,不是诗歌。诗歌之所以自然地出现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而不显得散乱,是因为诗歌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而歌词来自更广阔的世界,意义多重多样,而且还伴有熟悉的旋律,所以当歌词变成文学时,它的旋律性便被突然猛烈地剥夺了。它供读者的眼睛观赏——这意味着一种选择性行为——而不是供读者耳朵聆听了。如果单凭耳朵聆听的话,一首歌的歌词也许会在一个寻常的早晨偶然被人听到,从而令人印象深刻。但当歌词变成文学供人阅读,这种偶然便消失了,尽管我们仍然会尝试从纸张之间寻找这样的美妙时刻。
收录歌词的书籍如今成了一项火热的生意,尤其是那种装帧精美,制作昂贵的。这一潮流是Faber&Faber出版社在2011年率先开创的,他们出版了一本贾维斯·卡克(Jarvis Cocker)的歌词集,照片上贾维斯·卡克穿了一件古色古香、棕黄相间的防尘夹克。“贾维斯·卡克”这几个字的字体刻意与出版社诗歌集的标题字体保持了一致,反映出了像贾维斯·卡克这样的音乐人在流行文化中已经取得的地位。的确,为什么不把歌词与诗歌相提并论呢?如今,流行音乐的确够得上这样的位置,这一点是有坚实的标准依据的:只有那些老套的反对者才会辩称,鲍勃·迪伦(Bob Dylan)叙事动人和社会分析尖锐的歌词作品还是缺乏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分量。像萨福、品达这样的诗人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创作有关个人情感的短歌,他们弹琴作词,并称之为抒情诗。其实如果当时有条件,他们也大可以把自己作的歌词用限量版的大理石黑胶唱片发行出去。
当然出版业的这股潮流也是在迎合热爱怀旧的中年消费人群,对于这些人来说,流行音乐家曾是他们的人生导师和偶像,他们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对新世界的睿智洞见表达出来。真的,我没有在开玩笑。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这些流行音乐家仍旧是令人崇拜的存在,尤其是在一种崇尚表达的文化之中。然而,歌词与文学之间的紧张气氛依然存在,正如迪伦在2017年6月的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歌词不同于文学……歌词可以在我们的世界里更生动地表演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歌词变成文学时,某些东西就会流失。尼尔·田南特(Neil Tennant,宠物店男孩乐队成员)在介绍他的书《一百首歌词和一首诗》(One Hundred Lyrics and A Poem)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书本并不是歌词最自然的栖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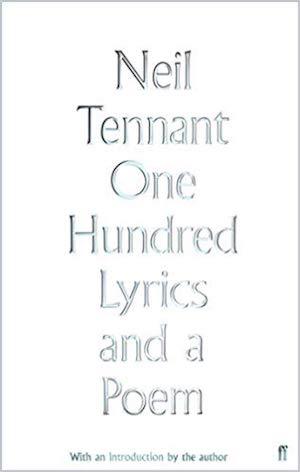
《一百首歌词和一首诗》
田南特在成名之前曾任漫威漫画和音乐杂志《Smash Hits》的编辑,这段工作经验让他学会了“如何让文字变得更简洁有力……我可以把这种方法也运用到歌词和整个歌曲的创作中去”。这个办法听上去着实不太浪漫,它所营造的情绪会影响整个歌词,因为无论多么美妙或是忧郁的歌词,常常一写到纸上就都变得冷冰冰了。以1985年的《西区女孩》(West End Girls)为例,这首歌让30岁的田南特一举成名,他的灵感来自于TS·艾略特(TS Eliot)的《荒原》。这一对句“if when why what/How much have you got?”听起来像是对撒切尔主义的完美分析,它自带一种上扬的音调,有着歌手故乡北希尔兹(North Shields)的影子。然而歌词一旦落入纸上,它便失去了这种昂扬的语调,只剩下无比沉重的文字本身。
总的来说,田南特精细的英伦风格需要一些更为大胆的东西来抵消它的简洁性,而当他的歌词落于纸上时,你就听不到另一位乐队成员克里斯·洛韦(Chris Lowe)加入的那些美妙的合成器声,感受不到那些涡轮般的迪斯科律动。田南特还按字母顺序排列了他的100首歌词,这似乎是一种非常随意的处理方式。美国创作歌手威尔·奥尔德姆(Will Oldham)也曾使用这种方法出版他的歌词集《爱与恐惧之歌》(Songs of Love and Horror),他像田南特一样,在每首歌词后添加了简短的传记脚注。他的书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我对他的歌曲本身知之甚少。也许一个人因为自己喜欢的歌词而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才是这里真正的问题所在。
为了对真正的歌词爱好者负责,一本歌词集必须包含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摘要。也许歌词集是一种更抽象也更为艺术的自传。当这些成分进入田南特的书中,它的意义便更为宽广了。他提到业余戏剧公司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写作产生了兴趣,这一点很让人着迷;他也曾对恋人说过“你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会说你爱我”,2000年的一首歌里就是这么唱的。他还讨论了单词发音的方式:1990年的《做无趣的人》(Being Boring)的标题就来自于一篇直白的日语评论文章,田南特表示:“我喜欢这个短语有弹性的节奏。”
田南特的歌词在出其不意时效果最好,就像我十岁时在《顺其自然》(Left to My Own Devices)中听到“切·格瓦拉和德彪西随着迪斯科节拍起舞”这句歌词时那样,那时这首歌还没有火。因此,毫无疑问,这本书最好的部分也是那些出其不意的句子,即书结尾的那首诗:四行简单有力的诗句,探讨了我们生命终点的不可知性(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反正这首诗能值回书的价格)。这首诗证明了他本质上是一名优秀的作词家,他懂得那种出其不意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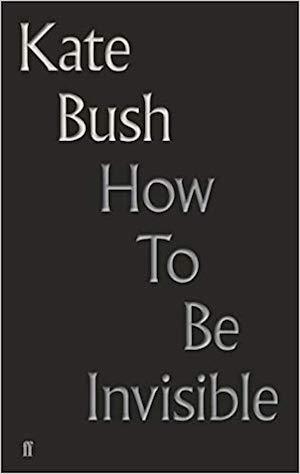
《如何隐身于世》
也没有人比凯特·布什(Kate Bush)更明白这种力量,她是Faber&Faber出版社作词家名单上的首位女性。在她之前的有贾维斯·科克、比利·布拉格(Billy Bragg)、范·莫里森(Van Morrison)和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肖恩·赖德(Shaun Ryder)的《快乐星期一》(Happy Monday)在她之后出版。与田南特不同,凯特·布什的作品都像有魔力一般,可能是因为她的歌词结构大都很奇怪。她还在简短的作者笔记中补充道,“所有歌词失去了音乐的陪衬时都被视作是诗歌作品,因此歌词出版后会比它们最初在专辑中突显出更为丰富的意义。”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发现她有时只不过是在玩弄像“o'er(即over)”这样的诗歌结构。然而,要公正地评价她的作品,我需要花几周的时间聆听专辑,以促进对这些歌曲更深层次的理解。很显然,布什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布什在《如何隐身于世》(How To Be Invisible)中也给自己的歌词归了一些类,但是却没有明确地解释:要靠读者自己去发现每一页歌词之间的联系。有一些歌词是关于云的(“破云”“天空”“你想要炼金术”),这些字眼不时迸发出现。还有一些明里暗里谈论战争的歌词(“拔出别针”“呼吸”“四号实验”)。《军队梦想家》(Army Dreamers)也在其中,这是众多在纸上读起来也力量充沛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在1980年非常火,歌词有关于一名阵亡士兵,让人想起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提出的残酷经济,其中最有力的一句是:“现在他安坐于自己的墓穴里,倒不如当初在家捯饬纽扣和弓箭呢。”
有一些主题会不定时地再次出现在她的歌词里。比如《坐在你的腿上》(Sat in Your Lap)中把恋人紧紧绑在一起的“绳子”意象,在《大雪降临惠勒街》(Snowed In At Wheeler Street)中幽灵般地再次出现了(这两首歌分别来自1981年和2011年,具体日期在书中并没有写出)。凯特·布什的两张专辑《爱的猎犬》(Hounds of Love)(1985)和《空中》(Aerial)(2005)的B面——分别是《第九波涛》和《甜蜜天空》——也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彼此产生着共鸣(《第九波涛》中对溺水女人的低语用不同的字体写满了两页纸;而在《甜蜜天空》中,小鸟的歌声部分用的是一种活泼尖细的字体)。凯特·布什是一位艺术家,她自始至终都在不断探索歌词形式的种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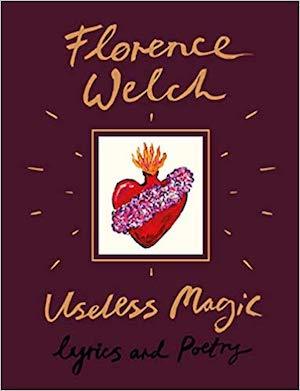
《无用的魔法:歌词与诗歌》
在《无用的魔法:歌词与诗歌》(Useless Magic: Lyrics and Poetry)一书中,Florence And The Machine乐队的主唱弗洛伦斯·韦尔奇(Florence Welch)也向布什表示了致意。布什的《Babooshka》这首歌被列为韦尔奇早期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书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韦尔奇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她在夏特马尔蒙特酒店的信纸上一笔带过自己取得的成就。
这是一个自我意识极强,极其成熟的年轻人所创作的“剪贴簿”。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照片就贴在一张在派对上看到一个男孩的利弊清单的旁边(“他会记得他有多喜欢你”,“她可能会在那里”)。这给这本书增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诚实感,歌词的构思也是如此:“我们正准备出去/我嘴里像有烟花一样畅快。”韦尔奇经常犯一些拼写错误,比如宗教十字架(crucifix)她写成了“crusefix”,天空的复数形式(skies)她写成了“sky's”,但这无伤大雅,她自己也承认,她在诗歌方面的尝试质量还是参差不齐的。最后一首倒是很好,标题很简单,叫做《我写不出来这个》。“现在总的来看/过于成熟/也过于悲伤/过于‘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而不能写成一首诗歌了。”她悲伤地写道,她抓住了语言的顺滑感,以及大众对这种顺滑感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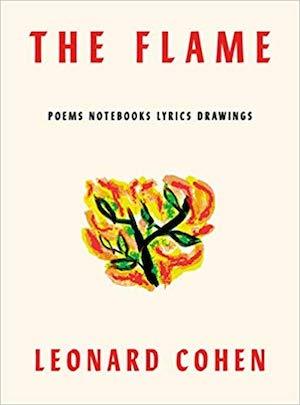
《火焰》
作词家一直在与这个问题作斗争,就像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一样。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火焰》(The Flame)描写了一个人坚持活到生命的尽头时的表现。科恩的儿子亚当在一篇感人的介绍文中回忆说,有一天在寻找龙舌兰酒时,他在父亲的衣服口袋、抽屉和冰箱里发现了许多笔记本。原来科恩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创作诗歌和歌曲。直到最后他都觉得自己最著名的歌曲《哈利路亚》还未彻底完成。
所以,这本书中最感人的片段之一是科恩和他的朋友加拿大诗人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之间的一封邮件,这是多么出乎意料的可爱啊。这几乎就像一场说唱之战,两个老家伙在用小写字母争论黑暗的概念。“他会让它变暗/他会让它变亮/根据他的律法/这是莱昂纳德没有写的。”科恩开玩笑地反驳道。一个月后他去世了,但他说过的话仍然在世间流传。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些话带到更多的地方,而不只存在于书本之中,让这些话陪伴着世人前进。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