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我们应该缩减三分之一的工作日
如今,自由民主已在广大群众的颓丧情绪中摇摇欲坠,一些强硬的政治观点开始被人们当成常识和真理看待:在全球市场中,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提高生产力;国家的福利范围覆盖太广,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削减一些福利;外来移民已经超出控制,因此我们的边境线必须加强把守——这些成为我们接收的“真理”。
我们面前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一种全新的规则与模式,要么便得冒着让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和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领导人)之流掌权的风险。政坛的中心地带一会儿被拽向左,一会儿被拉向右,结果在中间坍塌了。与此同时,所谓“进步的政治活动”也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居庙堂者只一味反对别人提出的政治主张,自己却丝毫未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我们的愿景、追求和信仰都去哪儿了?
在这幅黯淡的画卷里,有一本书和它的作者乘风破浪,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乐观和答案。鲁特格尔·布雷格曼是一名28岁的荷兰人,他的作品《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已经席卷荷兰,书中传递的理念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他提出的解决方法相当简单,但与当今世界的大潮背道而驰:我们应该设定一个全民统一的、能够满足每个人温饱的基本收入定额——比如说每年1.2万英镑;每周的工作时间应该被削减到15小时;国家的边境线应该对外开放,并且允许移民随意选择他们想去的国家。
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制度都只是天马行空,但其实布雷格曼搜集了许多过往经验与案例来支持他的理念。更值得一夸的是,他这本书里并不全是枯燥的数据分析——当然,他也不会刻意回避那些真实数据。书中充满了热情、智慧和想象力,并有一种魔性的说服力,即使是在你并不完全相信自己读到的内容时也会心悦诚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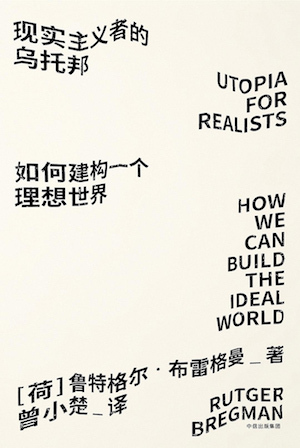
《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著 曾小楚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11
布雷格曼住在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这大概算是荷兰最主张进步的一座城市了。在这里,自行车基本上是人们唯一能够使用的交通工具,骑摩托的人会被视为有罪。这座经精心规划的小镇中部流淌着一条美丽的运河,布雷格曼的家就在运河边,离它只有几码的距离(1码约为0.9米)。
布雷格曼身材消瘦,面色苍白,脸上有几根细小的胡茬,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8岁还要年轻。但当他谈起自己书的主题时,语气里则充满了威严。布雷格曼书中的内容展现了他的成熟和睿智。他没有一味地攻击资本主义和后启蒙自由主义,而是在书的开头先赞扬了它们的成绩。他向读者展示了人们的寿命、健康水平、财富数、教育水平和自由度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巨大提升。
“我认为左翼存在的最大问题,”布雷格曼说,“在于它只知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它反对财政紧缩,反对社会现存的权力结构,反对‘恐同’,反对种族歧视。我并不是在说我不反对这些,而是我认为你也应该有自己支持的东西。你需要有一个新的愿景,计划自己未来的去向。”
布雷格曼就有自己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很清晰。但让我们先等一等。全民统一的社会福利、每周工作15小时、开放边境线,这些都是认真的吗?怎么去实现呢?
“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说我的想法不切实际、不可理喻,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实现这些制度,”他说,他将在后面给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答复,“我会这样简单回答‘噢,那么你想坚守现在的制度吗?现在的制度又带来了多少好处呢?’”
布雷格曼的祖国荷兰最近面临着一系列危机,于是主张不再接收穆斯林移民,封禁《可兰经》的基尔特·威尔德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政客。在这个曾是欧洲最兼容并包国家的论战变得越来越不和谐。现在的情况尽管不容乐观,却还是无法解释设立一个全民基本收入标准的意义何在。“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布雷格曼说,“扶贫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每个国家的投入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数都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5%。但是提高一个国家所有贫困人口的基本工资的投入只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

基尔特·威尔德斯 图片来源:Dylan Martinez/Reuters
理论上也许没有错,但他毕竟是在要求国家每年发给每个国民(无论贫富)约1.2万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这要怎么实现呢?这就要求中产阶级缴纳相当高的赋税,高到几乎与其所得收入相抵,而极富裕阶层的税率则需要设立得更高——但这种政策尚没有成功的先例,因为有钱人都极其善于保护自己的财产。
布雷格曼对这个论点的阐述有些模糊。他说,即使是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曾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表现出极大兴趣,当然,他们更喜欢称之为“负所得税”。他还注意到,曾经最有可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国家是美国,当时在任的总统是尼克松。只是当时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认为尼克松并没有准备足够的资金来支撑这种制度,所以这项政策在最后一刻被否决了。
布雷格曼承认,建立一个真正惠及全民的制度,需要首先对税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此外还需要公众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但你必须先找到一个切入点,在他看来,最好的起点就是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形式。
“英国的一次投票显示,37%的英国从业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存在的必要。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有清洁工人、护工和教师,还有咨询顾问、银行业者、会计、律师等等。这其中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激进。我们完全可以把工作日缩减三分之一,但还拿跟先前一样的收入,或者更多!”
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不重视自己的工作,就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他们的工作是无形工作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才能正常运作。他们不能就这么把自己剥离出去。
“这就是我们能得出的最好结论吗?”他被我乏味的实用主义思想震惊了,“人们总说:‘我感觉自己孤立无援,我觉得我的工作一无是处。’我们只能这么回答他们:‘不,不,你的工作用处很大。你要相信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我们付给你这么高的工资,你的工作肯定是有意义的!’”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布雷格曼说,“就是不能一成不变。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和福利体系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布雷格曼的父亲是荷兰南部小镇的一名新教传教士。他大学主修历史,希望成为一名学者,但后来他觉得那样的人生过于与世隔绝。于是他开始做一些记者工作,却发现新闻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新闻往往只报道异常事件——恐怖主义、腐败、危机等——对于事物的日常运作方式却只字不提。
所以他在《通讯时报》(The Correspondent)找了份工作,这是一家新的报社,他在这里可以把新闻写作和学术写作相结合,以一种新的笔触描述这个世界。这种混搭的文风让人想起了《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他的文章富含大量引人入胜的奇闻异事,这些轶事后面通常会附上许多来自调查研究和学术论文的信息资料作为背景支持,但他把这一切都解读得清晰易懂,因此可读性极强。
但布雷格曼的理想主义还有这样一个层面:他坚信每个人本性善良,因此只要有对现实的合理分析和政府的妥善管理,就能实现最为深远持续的变革。他反复提出,民主、性别平权、废除奴隶制等理念,都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
他在书中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那段关于乌托邦的著名表述,并对其表示赞同:“一幅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漏了一个国度,而人类总在那里登陆。当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四处眺望,又看到一个更好的国度,于是再次起航。所谓进步,就是去实现乌托邦。”(摘自《谎言的衰落》,萧易译)
但乌托邦总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变成反乌托邦。布雷格曼意识到了这样的威胁,他在评估共产主义实验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他同时也认为,在重大改革中,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有时也会是良性的。我注意到他在书中提到,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让原本的低收入人群拥有上学读书,以及应聘自己喜欢工作的机会。但问题来了,这样的话谁来做清洁工呢?
他听到我的问题,露出了笑容。
“我认为,关于基本收入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它不仅是对收入的再分配,也是对权力的再分配。这样一来清洁工在讨价还价时就有了相当大的主动权。举个例子,在大学里,清洁工的工资将会比教授更高,我认为这是件彻头彻尾的好事。教授热爱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额外的钱作为补偿。而清洁工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能获得更多的酬金!”
我提醒他,这些历经万难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可能不会认同他的想法。但他给了我一个答案,其中体现的理念打消了我的疑虑。“基本收入能够给予人们最重要的自由:自主决定想去做的事的自由。”
我能想象得到,许多资深人士会对这位几乎没见识过这个错综复杂世界的年轻人的才智表示质疑。但布雷格曼的理念很清晰。乌特勒支和荷兰的其他几座小镇已经遵循他的主张,开始试行基本收入制度。芬兰也开展了试行,但对象仅限于无业人员。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法夫的议会均已开始草拟方案,瑞士也对此表现出了兴趣。英国的影子内阁大臣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表示现在“也许到了该把这种理念付诸现实的时候了”,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贝努瓦·哈蒙(Benoît Hamon)也把布雷格曼的理念写到了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准备的竞选宣言里。就连被公认有远见、靠技术发家的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都对其表示了认可。

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是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支持者 图片来源:Ringo HW Chiu/AP
马斯克支持基本收入理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不远的将来,由于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工作岗位很可能会严重不足——这也可以作为削减工作日的原因。从某种角度看,人们对布雷格曼关于工作日时长的理念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历史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也走了有一段时间了。如今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以及何时才会承认这些不可避免的现实。
然而,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布雷格曼的书中并没有提及。比如说,众所周知,专业技能通常需要通过高强度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那么会有人愿意乘坐由飞行时数有限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吗?病人会让手术经验有限的外科医生替自己手术吗?
布雷格曼在回答中指出,劳累过度的飞行员和外科医生也容易造成事故。他补充说,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工作”,工作的意义应该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对这个社会做贡献。
这对我来说有点过于乌托邦化了。但如果退一步,仔细考虑我们的现状,会发现重新定义“工作”毫无疑问是完全合理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高但表面上却并没有创造任何实际价值的工作而言。读者在阅读《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时,思绪很容易会飘到广告经理、管理顾问、外汇投资人,甚至是专栏作家身上去,好奇这些工作究竟创造了什么效益。
布雷格曼最薄弱的论点大概是关于开放边境线的那一条——并不是因为它将在长期内都无法实施,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分析这个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人口密度问题——如果再有上百万人来到已经十分拥挤的荷兰,那么整个国家的局势会迅速变得非常紧张,除此之外还会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麻烦;第二,文化冲突问题——从一个文化背景到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会给民族同化带来真正的困难,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对这些困难深有感触;第三,在相对穷困的国家,最有可能移民的是国内的较富裕阶级,开放边境线相当于把这些国家最不可或缺的中产阶级直接送走。
听完了我的观点,布雷格曼说,对他而言,开放边界线并不是明天就能实现的事,这他很清楚。这是一个理想,是奋斗的方向。这句话其实对他的所有观点都适用。但最关键的是,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目的地,为那些在现下的四面楚歌中主张进步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努力的目标。
没错,他是一个空想家,但也是个实干家。他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但最首要和最困难的一点是,要相信既成的一切是可以改变的。让我们期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的表现吧,未来的他将有可能重塑我们的未来。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