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巴革命者书单: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阅读趣味
甚至连古巴革命的标志性人物切·格瓦拉也不得不承认,无休止地跋涉马埃斯特拉山脉是有局限的。他在《切格瓦拉论游击战》(Guerrilla Warfare)中警告未来的革命者:“游击队战士的生活中也有无聊时光。”他说,要想克服无聊导致的危险,最好方法是阅读。许多反叛分子都受过大学教育——格瓦拉是一名医生,菲德尔是一名律师,其他人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前往叛军丛林营地的游客常常被他们的文学倾向所打动。即使是最有男子气概的战士,似乎也会被人看到蜷缩在书本上。
格瓦拉建议游击队要携带一些非虚构作品,尽管这些书往往颇有分量,但“优秀的英雄传记、历史或经济地理书籍”能够防止他们沉迷于赌博、酗酒等恶习。难以想象的是,早期军营里最风靡的书是一本西班牙语的关于美国历史上伟人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1957年访问格瓦拉军营的CBS电视台记者罗伯特·泰伯(Robert Taber)发现,这本书在军营中如此受欢迎可能是由于格瓦拉的推荐。文学小说也同样受欢迎,特别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与革命框架相契合的小说。最热门的小说之一是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Curzio Malaparte)的《皮》,一部讲述二战后那不勒斯被野蛮占领的小说。菲德尔曾经坚信革命会取得胜利,因此他认为读这本书有助于确保革命队伍在占领哈瓦那时表现良好。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只会引起现代藏书家注意的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的心理惊悚小说《人面兽心》也被翻烂了,被他们全神贯注地钻研。

《皮》[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魏怡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2
菲德尔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是一位充满灵感的排长。他曾在日记中回忆,一天早上,当他正埋伏等待时,因沉迷于“塞弗林(Séverine)与司法秘书长的第一次对话”,结果被八点过五分的第一个枪声吓呆了。格瓦拉也曾因为全神贯注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一次空袭中差点儿被炸死。
夜里的几个小时也可以用来听故事。两位乡村诗人甚至开始吟唱游击队版本的诗歌集。一位名叫何塞·德拉·克鲁兹(José de la Cruz),外号“克鲁希托(Crucito)”,这位农民自称“山中夜莺”,用十节诗节的guajira(山中农民)创作了史诗歌谣,讲述游击队的冒险经历。他就像丛林中的荷马,带着管笛坐在篝火旁,吟诵着使人发笑的词句,同时把他的竞争对手卡里克斯托·莫拉莱斯(Calixto Morales)斥为“平原秃鹫”。不幸的是,吟游诗人克鲁希托后来在战争中被杀,口头诗歌的传统就失传了,而且并没有足够多的空白纸张记录下了他的诗作。
但古巴革命中最令人着迷的文学细节的一段,是菲德尔在接受西班牙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尼(Ignacio Ramonet)采访时的断言。拉莫尼说,他曾研究过海明威1940年的经典著作《丧钟为谁而鸣》,以获得游击战技巧。菲德尔说,海明威的小说让他和他的手下“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把那次经历……看作是一场非常规的战斗”。他补充说,“这本书成了我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回看它,求教于它,寻找启示。”
作为一位著名的旅居海外的美国人,海明威当时在古巴广为人知,这部小说是根据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担任报社通讯员的经历写成的,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敌后的非常规战斗。他在旧哈瓦那殖民时期的世界酒店511房间里,用雷明顿打字机打出这份手稿的。他从未想过,一场类似的战争会在他的第二故乡打响。尽管这本书是在菲德尔和他的革命同志们还年幼的时候出版的,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这本畅销书非常了解(该书西班牙语译名为《Porquién doblan las campanas》),更不用说由加里·库珀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了。菲德尔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学生时代,他说他在马埃斯特拉山脉至少重读了两遍。
但当涉及到具体的游击战术时——比如伏击的艺术,或者如何管理补给线,《丧钟为谁而鸣》并没有提供太多具体的见解。书中倒是有一些简单明了的想法,比如,在手榴弹别针上绑上绳子,这样就可以远距离引爆,或者关于理想的游击队藏身之处的描述。但更重要的是,这本小说是一本描述非常规战斗心理因素的颇有洞见的手册。主人公罗伯特·乔丹被迫在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中穿行,这个世界充满了异国情调和随时可能出现的背叛,就像菲德尔的手下在马埃斯特拉山脉中经历的那样。把语境转入热带环境的设定,从部队中保持积极态度的重要性到罗伯特·乔丹适应拉丁文化的相处规则,小说和叛军的处境有许多相似之处:“给男人烟草,别打扰女人。”这体现了菲德尔牢不可破的军规,即村里的女孩永远不受骚扰,游击队的主要组织者西利亚·桑切斯(Celia Sánchez)也在坚持不懈努力,为男人们提供像样的雪茄(当然,罗伯特·乔丹在小说里坏了规矩。他与迷人的玛利亚的火热恋情,包括丛林嬉戏的细节描写,只能给渴望爱情的游击队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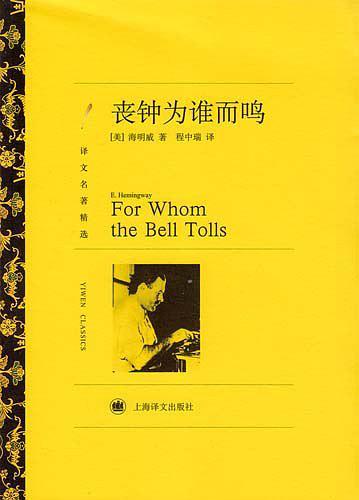
《丧钟为谁而鸣》[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程中瑞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5
尽管海明威肯定会为古巴叛军阅读他的作品而感到高兴,但对于自己第二故乡的革命,他却异常缄默。他的渔船船长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Gregorio Fuentes)后来夸口说,他和海明威曾在他们的“比拉号”船上为菲德尔走私枪支,但这似乎是为游客编造的无稽之谈。在私底下,海明威对古巴的独裁统治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不屑一顾,并在一封信中骂他“狗娘养的”。但海明威唯一一次公开抗议,是在他把自己的诺贝尔奖奖章捐赠给古巴人民时:他没有让政府机构展示它,而是把它留在维尔根·德尔考布雷(Virgen del Cobre)大教堂保管。它至今仍在那里,保存于一个玻璃箱中。
就连巴蒂斯塔自己的情报机构也难以相信海明威是中立的,有好几次,当他外出旅行时,士兵搜查了他在哈瓦那的官邸,也就是著名的“维吉亚庄园”(La Finca de Vigía),寻找武器。有一次,闯入者被海明威最喜欢的狗——一只名叫布莱克的阿拉斯加施普林格猎犬攻击。他们在吓坏了的仆人面前,用枪托把它殴打致死。布莱克被埋在游泳池旁花园中的“宠物墓地”里,那曾是它依偎在主人脚下多年的地方。回到哈瓦那后,海明威不顾古巴朋友的警告,愤怒地冲进当地警察局报案。如果报案的是一个当地人,他可能会被打一顿,但海明威的名气保护了他——尽管,毫无疑问,没有任何调查结果。顺便说一句,布莱克的坟墓还在维吉亚庄园,不过这些信息并没有透露给前来参观的源源不断的书迷。
在1959年的“蜜月期”,当整个世界都被菲德尔的浪漫胜利所吸引的时候,一群想要亲自观察革命的文学名人拜访了海明威,其中就包括《巴黎评论》年轻的创刊编辑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一天下午,海明威和普林顿在他最喜欢的哈瓦那酒吧埃尔·弗洛里迪塔里,与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和英国评论家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一起喝台克利酒时,他们撞见了负责监督处决巴蒂斯塔最邪恶追随者的警官。普林顿和威廉姆斯都很内疚地接受了当晚参加行刑队的邀请——这是海明威极力鼓励的一种病态的、窥淫癖的冲动,因为正如普林顿后来回忆的那样,“重要的是,只要作家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反应,他就能接触到几乎所有的东西,尤其是人类的过度行为。”
碰巧的是,行刑被推迟了,两人也未能完成那场可怕的邀约——这对文学来说无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来源:界面新闻)

